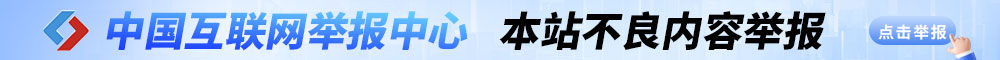|
记忆中的光辉——致敬陈召彬主任 子月 1973年3月18日,春光如诗,我的心境也随之明媚开朗。我骑着自行车,载着简陋的生活必需品,径直奔向了丰县原种场——一个位于赵庄镇政府北约两公里处的地方,如今已更名为黄楼农场。 会计室位于三间西屋内,而堂屋则大门紧锁,东西两侧尚无围墙环绕。步入其中,空无一人,唯有小猪崽的啼叫声打破了宁静。 循声而去,只见东边矗立着一座低矮而宽厚的猪圈,门朝南开。走近细瞧,一位年约二十的青年正面朝南方站立,他瘦脸微黑,头发略显蓬松,身着灰布衣裳。他的短靴与裤腿沾满了泥粪。而在他对面,则站着一位中年男子,他浓眉大眼,额头光洁,面色苍白却透着睿智,眼中略含焦虑与忧愁。他身着一套得体的银灰色中山装,圆口布鞋同样沾满了粪泥。“是来报道的吧?”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无需回答的笃定。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“嗯”,轻轻点头说道:“会计室没人。”“这样吧,我先去给小猪崽量体温,顺便把张会计叫来。”他边说边迈步前行,“陈主任,我就不跟您去了。”那位蓬头青年说道。 次日,阳光明媚,我前往食堂窗口排队打午饭。菜品有两样:一样是黄豆炒萝卜丁,每份三分钱;另一样是猪肉粉条萝卜丁,每份一角钱。我选择了前者,端着碗走到食堂前的空地上,刚蹲下身来,陈主任也端着碗到了,他的菜同样也是三分的。饭后,陈主任像填写履历表一样详细询问我,我则尽可能详尽地回答。 后来我才得知,全场二百多人,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脱口而出,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他都了如指掌,甚至每个人的文化程度、性格特点和特长,他都铭记于心。 问过话后,陈主任向茶桶走去。我紧随其后,只见他弯腰接了大半碗茶,用筷子搅动几下便一饮而尽。看到我后,他微微一笑,又走到井边的清水桶旁,舀了半碗水,同样用筷子搅动几下后倒掉,随后快步向宿舍走去。 如今看来,这位科级干部喝刷碗茶的行为或许显得荒唐,但在当时却是机关里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 当时我负责管理着六亩棉花地,共六行,地长四五百米。松一遍土需要三天时间。那时,我见到有员工用牲口拉耘锄松土,既省时又省力。 6月27日,我借来一匹骡子和一把耘锄来到地头,驱赶着骡子前行。然而,仅走了四五米远,就锄掉了三棵棉花。又前行了三四米,又有一棵棉花被歪倒。前进不得,若是后退,骡子加上耘锄,这片棉花恐怕都得倒下。后悔、懊恼、沮丧、自责,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,让我心中五味杂陈,失神地站在原地。 “没使唤过牲口吧?”一个声音传来。“没有。”我苦涩地回答。“来,我教给你。”说着,陈主任从我手中接过耘锄,“看着,双手握把,松紧适度,用力均匀,控制缠绳是关键。左缰紧,牲口左行;右缰紧,亦然;两缰绳一样长,用相同的力,牲口才会直行。”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,前行了一百多米后,他把耘锄交还给我。又前行了百多米,见我基本掌握了要领,他才含笑走向另一块田地。 还没到正常的收工时间,地里的活就已经干完了。我心情舒畅地赶着骡子回场。“叮铃铃……”一辆自行车迎面驶来。车刚过我身旁,骡子便突然奔跑起来。我奋力向后拽住缰绳,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。若是松手,锄毁骡伤;若是碰到人,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或许是我慌乱中抓到了缰绳,或许是骡子意识到已经到了吃住的地方,它渐渐放慢了脚步。我惊恐、疲惫、茫然地躺在床上,头皮发麻、脑袋发胀。 “起来吧,饭给你打来了。”随着声音传来,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。我愕然地睁开眼,只见陈主任弯着腰站在我面前,他白净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,紧绷着嘴,明亮的眸子里满含关切。“还在害怕吗?骡子奔跑的情景我看到了,但离得太远。”他顿了顿又说,“好在没受伤害,吃一堑长一智,以后……”说着,他又一次抚摸我的头。陈主任那没说出来的话,我能猜得出。他温暖的手、关注的目光以及那散发着香气的饭菜,传递给我的是慰勉、嘱托、希冀以及深切的关心。我心中涌起一股酸楚,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 食堂前三十米路西的屋山头上有一块黑板,高约三米、长约四米。黑板正中上方写着粗重的仿宋体字“黑板报”三个大字,彩色图案将黑板等分为左右两块。左边通栏标题是“技术指导栏”,右边则等分为两块:左边是“国家级英模栏”,右边则是“本场光荣榜”。 陈主任和场首席技术员曾广前共同管理着一块十五米见方的试验田。棉苗移栽后,他们俩几乎每天都细致观察、记录。早期主要关注株高、叶阔、茎色、土壤湿度和温度等指标,并指导员工松土保墒、防止土壤板结以及防治棉苗枯萎等问题;中期则重点观察并记录棉蚜虫、棉铃虫的发生和发展周期变化,采取科学高效的预防和防治措施。全场上下一盘棋,统一时间、统一用药、统一配方,既为国家节省了资金,又减轻了员工的劳动负担。 在“英模栏”里,陈主任用工整的楷书书写着焦裕禄、王进喜、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以及雷锋日记和大寨精神等内容。这些事迹教育人、精神鼓舞人,焕发出了员工们昂扬的斗志。 而在“光荣榜”里,人物名单不断更新:有员工探索到了棉蚜虫的发展规律、有员工找到了控制棉花旺长的方法、有员工帮助生病的同事加班劳动保住了全场第一名的先进称号……这块小小的黑板报成为了员工们每天的必到之地。在黑板报前、宿舍里,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谁成为了技术能手、谁成为了植棉骨干以及要向哪些人、哪些单位学习。领导和员工之间、员工和员工之间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、互相敬重,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,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——那就是为国家多做贡献、为集体争得荣誉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洁得如同清晨绿叶上滚动的露珠一般晶莹剔透、无任何杂质;单纯得似村妇手中的擀面杖一样朴实无华、没有一点邪念。 那段岁月,小小的黑板报不仅承载着陈主任的心血与智慧,更凝聚了全场员工的心。它如同员工们汲取专业知识的无尽宝库,也是滋养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,激励着每一个人争先进、当模范,将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心底。 在这片广阔的场区里,没有一堵围墙将我们与外界隔绝。即便是隆冬时节,牛羊猪鸭饲养场、仓库、棉垛以及轧花车间等各处都忙碌而有序。防火防盗、安全生产,每一项责任都重如泰山。每当夜幕降临,陈主任总是亲自巡查,尤其是轧花车间,他细致入微地检查机器运转情况,落实防火保暖措施,甚至关心到女员工的长发是否妥善挽起放入工作帽,衣扣是否整齐,鞋带是否系紧,口罩是否按照场里的规定用打包下角料布加厚。 有一次,陈主任发现丁庆东的口罩没有加厚,他瞬间变得严厉起来,责备的话语如同惊雷般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:“加厚,加厚,我班班对你讲,你耳聋了吗?灰尘入肺,你不要命啦?”那严肃的神情和严厉的批评,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。 调到轧花车间后,我第一次吃夜餐时,食堂里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、香味四溢的菜肴。正当大家欢声笑语时,陈主任的到来让气氛瞬间凝固。他满面笑容地与员工们打招呼,抖落身上的雪花,却并未多言便转身离去。我好奇地问身边的王师傅为何不与陈主任交谈,王师傅叹了口气说:“心疼啊,这夜餐是场里规定的免费餐,陈主任冰天雪地地出来巡视,比车间员工还辛苦,理应有一份加餐。但之前我准备过,却受到他严厉的批评,还差点给我调换了工种。” 回想起这些往事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在我村,有一位分管教育的副乡长,在1965年,他的儿子小学升初中时因差1.2分未能升学。当时升学率仅有30%,学校初榜时他的名字赫然在列,但乡长审核时却坚决划掉了。如果放在当下,这样的故事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。 1974年9月18日,我离开了农场,五十多年来再未回去过,也未曾再见过陈主任。我只知道他家在县城东南,但具体是套楼、金陵还是梁寨,至今仍是个谜。 然而,这五十多年来,我始终魂牵梦绕着那片农场,魂牵梦绕着那时的工资和艰苦的劳动环境。但真正让我魂牵梦绕的,是那时的风清气正,是人人为国、为集体尽心尽力、尽智尽能的无私奉献精神。 如今,灯下提笔,展纸书写此文,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。虽然与陈主任单独谈话的次数并不多,最长也不过二十分钟,但他那事必躬亲、率先垂范的作风,对党的忠诚,对事业的执着,对人的坦诚,处世的淳厚,律己的严格,以及高尚的情操,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。 我庆幸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遇到了这样一位诤友良师,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,一位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党员——陈召彬主任。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明灯。 子月写于2025年初春于白衣河畔
|